2007-09-28
最近公司忙于搬家,一个月前就开始打包,准备搬到新地方去,可是忙忙碌碌,几经变更,直到到现在仍在旧地方打转。
到新加坡后我亦经历了几次搬家,每次搬家就像从钢琴的一个键跳到另外一个键,一连串的搬家就构成了交响曲。
想当初,到新加坡时,幸得堂兄鼎力相助,在他家当了近半年的“厅长”。当厅长除了给人家带来不便外,自己亦多有不便。特别是那次周未,因感冒发烧,困倦极了,很想有个地方躺下休息,可是,周未不用上课、上班,大家都在客厅看电视。坐在沙发上,想打瞌睡都不好意思,我强打精神,眼皮还是不自觉地打起架来了。那时侯就特别想家,想起了父母妻儿,如有亲人在身旁,问寒问暖,寻医治疗,那该多好。
当了近半年的“厅长”,我离开堂兄家,到了罗氏公会会馆。那天下班后,来到芽笼的罗氏公会会馆,从会馆坐办(办事员)那里拿到锁匙时,已经很晚,不好意思再回堂兄家了。新加坡的天气热,晚上没有被帐没问题,只是会馆那间用于打麻将的,位于一楼到二楼之间的半楼间,里面的三张麻将台,每台的麻将都乱七八糟,地上尽是瓜子壳、烟蒂头等垃圾,凌乱不堪,根本无法入住。会馆二楼原先租给人家当卡拉OK,租户搬走已有好长一段时间,楼上到处都是蜘蛛网。灯,大多数都坏了,不亮。有个别亮的也是那种老化后的日光灯,一闪一闪的。有数处天花板掉了,显出很大的几个窟窿,黑洞洞的,怪吓人的。楼下由许多小的桌子拼凑成一个大会议台。正面墙上挂着罗氏祖宗的画像,画像下面有张供奉祭品和烧香烛的神台,神台的一边有座比人高的坐地钟。会馆大门的一侧堆放着办丧事的屏风、及其他边丧事的杂物。那晚,没别的地方可去了,我只好在楼下的会议桌上暂时睡一宿,我和衣而眠躺在会议桌上,旁边的座地钟,钟锤一晃一晃地发出“滴答、滴答”的响声,每半个钟打铃一次,发出很响的“当”声,正点时则会按几点钟发出几声连续的“当……”声,虽说已经很晚、很累了,但眼前好像有什么晃动似的,总是睡不着,那时我在想,如果我是水浒传里的赤发鬼刘唐就好了,定能在会议桌上呼呼大睡了。
第二天是周末,上半天班,下午收拾好一箱行囊,堂兄帮我载到会馆。时间尚早,我看到楼下有两罐不到半桶的刷墙剩下的油漆,就用那两半桶油漆将约六平方米黑乎乎的麻将间粉刷了一遍,使那黑房子焕然一新。二楼的角落有煤气炉、水壶等厨房用具,于是我又到附近的市场买了一个电饭煲和好些速食面,开始了快乐的单身汉生活。
在会馆过了两个月逍遥自在的独居生活。临近过年时,妻子带着女儿出来了。我在朋友的介绍下,与他的亲戚,亦是同乡,租了一间房。那间房实际上就是私人排屋里的杂物间,大约七八平方米,有门没窗,日夜都得开灯,开风扇,即使这样里面仍然热烘烘的。住在这样的环境,还真能锻炼人的意志。
经过半年多的磨练后,我们换了一个地方,第三次搬家就更上一层楼了。在大巴窑临近布莱德地铁站的119座二楼租了一套一房一厅。那本来是两房一厅的套房。早期政府组屋的设计独特,饭厅在厨房里面,厨房比房间还大,客厅则与厨房一样大,主人房与客房一样。因为当时政府规定,组屋不得全套出租,屋主自己至少得住一间。那屋主看上去是个四十岁左右,开马赛地豪华车的有钱人,据说他另有一套洋房,不需要到这政府组屋来住。因此,他留一间房养“鸡”。每星期会带女人回来混上一两晚。他们回来多数都是直入房间干他们的好事,基本上与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那里的左邻右舍也都挺友善的,有的后来更成为朋友。大巴窑交通方便,购物容易,生活倒也方便,大儿子也在那里问世了。
在大巴窑租房住了近一年,我们收到政府寄来批准我们租房申请的信。于是,我们又从大巴窑搬到了义顺第604座五楼,一套比大巴窑两房一厅面积大十多平方,实用面积达七十多平方米的两房一厅,这是新设计的一种组屋。饭厅与客厅相连,厨房小了厅堂大,主人房也比客房大,主人房里面有独立的卫生间。那座房屋建了大约四五年了,政府出租给我们的那套房,还没有人住过,不晓得为什么,有房屋闲置着,而我们向政府申请租房近两年才获批准。政府的租屋,里面空空如也,什么也没有,连地板都是凹凸不平的,我们只好买来地板胶,给地板贴上一层皮。再买了一套基本的床柜。至于其他的家具,如沙发、桌子、凳子,楼下经常可以看到人家丢弃的旧家具,别人浪费我环保,稍作修正,旧物重用,弥补家中的不足。跟政府租房除了便宜些外,更重要的是不受别人制约,可以自由地购置自己喜欢的家具和生活用品。
604客厅的窗是由四块透明的玻璃组成的,相当明亮。只是太靠近主干道的公路和地铁线,打开窗时,公路汽车和地铁的噪声一齐涌入,在客厅就无法谈话了。震耳欲聋的噪声最让人难以忍受。搬到义顺604座是我来新加坡不到两年时间里,搬迁的第五个地方。真是“在家千日好,出门半朝难”。出来打拼就得吃苦。
客厅的玻璃窗太过透明,对室内的东西一览无余,让人感到有如被观赏的动物,甚为尴尬。因此,人们都给客厅装上窗帘,平时窗帘都是拉上的。有一次不知何故,窗帘后面的客厅玻璃窗关上却没上锁,到了次日凌晨三四点钟,一位“黑君子”趁我们熟睡之际,偷偷来访。那时刚好妹妹从深圳来探望我,因天气热她与外婆带着小家伙睡在主人房的地板上。那“黑君子”搜刮了我的睡房后又去主人房行窃,不小心碰到了妹妹,妹妹惊醒后,发现有贼,大喊有贼,把睡在隔壁间的我惊醒了,我即刻起来,发现一个黑影仓皇地从客厅窗口窜了出去。后来我们开灯检查,发现我裤袋里的钱包不见了,里面除了一些钱外还有我的身份证等重要证件,钱丢了不要紧,身份证丢了却是个麻烦。所幸那只是个爱钱的“黑君子”,将钱拿走了后,把钱包和身份证等证件乱扔在客厅地上。
第二天上班时,同事们得知此事后都笑着说“地理先生冇屋场;算命先生半路亡;报警器的设计先生,差点家中被偷光。”技术先进,性能卓越,被广泛应用在银行、商场的报警监控器,正是近年来我独立设计的产品。我设计的产品在为别人监控着千万财产时,自己的家却入了贼,不能不说是具有讽刺意义的。当然,这套价格不菲的报警监控器,普通家庭谁会去安装,我家没什么比这更值钱的东西需要用到它来监控,自然没有安装自己设计的产品。
与政府签订的租房合约只有两年。那时正是临近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,大量的香港有钱人涌入新加坡,他们移民来新加坡,首先就是要买房,解决住的问题。香港的住房比新加坡贵得多,只要将香港的普通房子卖掉,就可以到新加坡买到很好的房子。房地产业由于香港人大量涌入购买,加上部分本地投机商的炒作,房子的价钱一日一个价地狂涨。比现在国内的通货膨胀、物价飞升还令人担忧。我们从国内出来,白手起家,没有积蓄,根本交不起买房的百分之二十的首期款。我们曾尝试与本地的亲戚朋友借,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是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,钱是可以生钱的,借钱谈何容易。后来还是来自国内的朋友伸出援手,助我们在同一地区的义顺712座的十二楼,购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实际使用面积68平方米的屋子。这种屋子的建筑款式与大巴窑的两房一厅一样,只是主人房多了个卫生间。
第五次搬家不同于前四次,不是只有箱子和袋子,而是有了大件的家具。在604跟政府租的是空房,我们不得不置了好些家具,如床、柜等,这次搬家虽然近,但不少大家具我们耐何它不得,不得不请搬家公司。
有了604受噪声干扰的经验,买房时便特别注意是否靠近大马路,我们买的屋子是离马路的较远的一端,不再受公路噪声的干扰,早晨能听到鸟鸣。一年多后小儿子在那里出生了。
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,市场萧条,公司倒闭,很多人失业了。由于这里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,一但失业没有收入,吃饭住房都成问题,不少人只好将住的大房子卖掉换成小房子,以度过难关。那时,没有多少人有能力买大房子,房地产业更是大受打击,转售市场大房子的价格一路下滑,小房子倒显得奇特的好卖。到了二OO二年,我们决定改善住房,将义顺712的房子卖掉,再另买一套比较大房子。
义顺712的屋子,我们买时已十三年的屋龄,加上我们又住了五六年,到我们再转卖时,屋龄已近二十年,那时由于大房子冷小房子热,我们的两房一厅卖出时,价钱基本与五年前购买时一样,没赚没亏。我们将转售得到的钱再垫上七八万元,在兀兰靠近海军部地铁站的其中一座九楼,买了一套现在住的实用面积104平方米,当时只有六年屋龄的三房一厅的屋子。
兀兰是新区,房子都是新建不久的,新屋新设计。我们住的地方由三栋楼围成四合院,中间是儿童游乐场。屋与屋之间的间隔也比义顺宽畅的多,屋底下的走道不再是两边都是露天停车场,汽车统一停在附近的多层停车场,环境远比义顺好。我们购买的那座屋子的前面有另一座屋挡住了主要马路的噪声,其环境比义顺712更幽静。而离地铁站也较近,不到十分钟就能走到。
第六次搬家比第五次搬家东西更多,因为那时经济衰退,不少人回国了或移民到别的国家。一位移居去加拿大的朋友,将他家的家具卖给了我们,搬家时几乎是两套家具。只好择优录取,将较好的留下。
不过数年,我们就搬了六次家。从地点来看,每搬一次家就北上一步,生活也改善了一步,搬家就像弹钢琴,由低音向着高音区滑去,奏出特殊的搬家交响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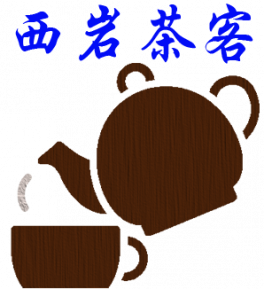
 Users Today : 2
Users Today : 2 Users Yesterday : 4
Users Yesterday : 4 Users Last 7 days : 25
Users Last 7 days : 25 Users Last 30 days : 103
Users Last 30 days : 103 Users This Month : 91
Users This Month : 91 Users This Year : 91
Users This Year : 91 Total Users : 12299
Total Users : 12299 Views Today : 2
Views Today : 2 Views Yesterday : 5
Views Yesterday : 5 Views Last 7 days : 52
Views Last 7 days : 52 Views Last 30 days : 226
Views Last 30 days : 226 Views This Month : 202
Views This Month : 202 Views This Year : 202
Views This Year : 202 Total views : 27144
Total views : 27144 Who's Online : 0
Who's Online : 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