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9月5日
奶奶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。往事如烟,三十年来,多少往事早已烟销灰灭。我与奶奶生活在一起的那段难忘的日子,许多事情也尘封日久。回乡祭祖那阵清风却掀开了我记忆中久违的一页,许多往事又一幕幕地浮显出来。
我的奶奶是位很普通、很平凡的农村妇女。因为爷爷去了南洋,数年才回来一次。奶奶不得不负起奉养公婆、教育儿女的全部责任。在奶奶的精心培养下,她的三个儿子—爸爸、五叔和满叔,都分别考入了名牌大学。毕业后都为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,他们都是获得高级职称的高级人才。在那时候,像爸爸那样三兄弟都都考入了名牌大学,成为高级知识分子。在我们周围乡里,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。因此,奶奶如“一腹三翰院”一样,在我们周围乡里很有名。
以前种田没什么化肥,主要靠猪屎、狗屎和人粪尿等有机肥。猪屎狗屎在农村就成了宝贝。猪是圈养的,只有狗是四处游荡,到处拉屎。为了使作物长得好,就要积肥。因此,大多数农民早上起来,都会提个猪屎畚箕到处去捡狗屎。为了抢先捡狗屎,奶奶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。有时候天还没亮,她就起来捡狗屎了。经常捡回一畚箕的狗屎,其中有不少是泥团、砖块。因为太早起来,天黑看不清楚。捡完狗屎回来后,奶奶又快快捷捷地煮早餐。吃完早餐,就到菜园劳动去了。从菜园回来,她会採回一大篮子或一担的蔬菜,足够一整天一家人吃的,还有喂猪的。
那年月除了菜园里还有点自由地外,其他的土地都是生产队的。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留下比别人更多的土地。只是我们家族的人大多数过番,或外出工作了,再加上未建成的新屋的两边横屋地,我们家的菜园子就比别人多了点。
我懂事时,奶奶大概六十多岁。她已不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主要是料理自家菜园。她勤劳,做事又快。她常在菜园里种菜、除草、浇水、施肥。我们家菜园里的菜比别家的都长得好。你看那白的、紫的、圆的、长的、大大小小的茄子挂满了茄树;吊瓜园里,青青毛毛幼嫩的,白白胖胖成熟的,“篮篮车车”,挂满了瓜棚;还有其他蔬菜,如葱、蒜、韭、荞等都长得“嫩嫩笋笋”。
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是典型的乡村生活。可是,有时到了黄昏,还能在菜园里看到奶奶的身影。
在我很小的时候,有一次跟奶奶去菜园。看到奶奶拔草,我也学着拔草。可是我拔过的地方不像奶奶拔得那么干净,还是“胡须马叉”,很多草的尾巴给我拔断了,而头仍留在土里。奶奶看到后,就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拔,才能将草连根拔起。我按奶奶教的方法做,果然不再拔尾不除根了。
奶奶做事情,总是特别麻利,特别快捷,特别干净利落。记得有一次,与奶奶一块去种番薯,奶奶插番薯苗的速度可快了。种番薯通常是一大一小,两个人配合。大人在番薯垅上锄开一个口(空穴),小孩则抓一把灰,往空穴里丢,大人再将番薯苗放入空穴里,提起锄头,让上面的泥土盖住番薯苗和灰。我配合奶奶放灰。奶奶插番薯苗的动作很快,很难跟上。我急得手忙脚乱,不时将灰丢到空穴的边缘。奶奶只好多花时间将灰扫入空穴中心,才能插苗。即使这样,奶奶也比别人插得快。
我们家门口是沐教、墩背、下湖洋等地去枫朗墟的必经之道。每年到了夏天,天气转热时,奶奶每天都会煮一大锅的叭子叶茶,让它凉后,装入大茶壶,大茶壶装不完的再装入一个类似小水缸的大瓦钵。第二天放在门口,供路过我们家的行人饮用。沐教、墩背、下湖洋等地人,常担柴去枫朗墟卖。他们挑着重担,走了五六里以上的路才经过我们家门口。此时个个都大汗淋漓,口干舌燥。他们放下担子,歇歇脚,再喝上一碗透心凉的、既解渴、又消暑的叭子叶茶,那感觉真是舒服极了,美妙极了!奶奶的善举,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敬。她在家乡一带是有口皆碑的好人,人们都知道洋梅坑有位好心的“拨元婆”。
有一天,墩背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到我们家喝叭子叶茶,那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孩,眼瞪瞪地看着我碗里的一条刚开锅的番薯。奶奶看到后,即刻叫我将碗端过来。那时我饥肠辘辘,正待热番薯凉些充饥。奶奶见我不太情愿的神色,遂将番薯折成两半,给那孩子一节。那孩子大概与我一样,此时此刻正饿着肚子呢。他高兴地接过番薯,“呼、呼、呼”地吹起来。待番薯稍凉,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在那三面红旗飘飘的年代,到处大闹钢铁,放大卫星,大跃进。粮食亩产不是几百斤上千斤,而是上万斤,十几万斤。中国好像一步就跨入了共产主义。大家放开肚皮吃大锅饭。只是好景不长,一年的粮,一二个月就吃完了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没粮食,人们不得不吃野菜,吃树叶,吃树皮甚至吃白鳝泥。那时饿殍遍野,全国不知饿死了多少人!
度过了三年饥荒难关的农民,仍然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。那时,农民种的谷子,大部分缴交了公粮、余粮,还有公社粮、大队粮、三超粮,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真正分到农民手上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。在丰年时,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力每月的口粮大约二十多斤谷子。灾年时,每月只有十多斤。大约是七十年代初,那年歉收,每个劳动力每月的口粮只有18斤谷子。不是劳动力的老人小孩的口粮则是 劳动力的六成至九成,即每月11至16斤不等。谷子去壳后,可得七成左右的米。也就是,我们村的口粮每人每月从7.7斤至12.6斤米不等。平均每人每餐大约不足一两米。除了逢年过节外,家家户户都是将仅有的一点米,多放些水熬煮成稀粥,好让吃完后,肚子有暂时撑饱的感觉。那粥之稀实非城里的人可以想像的,有人说稀粥是“一吸一条浪,一吹一条巷。”
为了使仅有的一点米不致于熬成清汤寡水,奶奶有一个好办法,就是使用“饭种”,所谓“饭种”也就是一碗粥而已。这碗粥的特别之处是在下一餐煮粥时,一起倒进锅里去重煮。这样就可以使新煮的粥比较快的粘稠起来,既节省时间又节省柴草,的确是个好办法。但是那艰苦的岁月,人们常处于饥饿状态,我们劳动回来,饥饿难忍时,有时也难免会把“饭种”给吃了。为了“饭种”不被吃掉,奶奶常将它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。有时想不起来,一下子还找不到呢。遇上天气热,“饭种”隔天就馊了。只要不是严重馊坏,奶奶都不舍得将它倒掉。
奶奶极“锡”子孙,下枫朗墟买块糕都舍不得自己吃,要带回来分给子孙吃。
尽管我们也不富有,但有五叔每月定时寄回的钱,满叔寄的钱,以及逢年过节时南洋汇回的钱,比起其他人,我们家相对好些。奶奶常常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穷苦人,她会想办法给那些需帮助的人一些吃的、穿的,如番薯、米粮、旧衣服之类的东西。
与为了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的人不同,我从未见过奶奶与人争吵。即使奶奶遭人欺负,她也不会与人争吵。而是默默地回到家里,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,口中念着:“主啊,……”,向上帝祷告。她遭受的委曲,似乎在这祈祷中就给化解了。
贫穷落后的农村,各种各样的神呀,仙呀,特别多。门有门神,屋有屋神,灶有灶君爷,神庙里有关帝爷,城皇庙有城皇爷,水口(村子的出入口)有伯公爷,就连探笕角的那个大石头,也常有人去拜祭,据说那是会保护人的“石爷”。与整天烧香拜神的农村妇女不一样,奶奶从不烧香拜神。这并不是说奶奶是个无神论者,而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。她颈上终年佩带着一个十字架,每天早晚都向上帝祈祷。世界上大多数宗教,如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,都是教人行善的。我猜想这十字架一定是奶奶的精神支柱,这十字架一定帮奶奶消除了不少烦恼,这十字架一定为奶奶阻挡了不少灾祸。
到了一九七五年,有一天,奶奶突然发病,嘴角歪斜,摇摇欲坠。爸爸见状立即将奶奶抱到床上。着急地呼唤着:“阿姆,阿姆……”。可是奶奶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,没有回应。此时奶奶已八十多岁高龄,得了这么严重的病,大家都非常担忧、害怕,甚至不得不考虑准备后事。当时,我们急忙去请了当地最有名的医生前来医治,医生检查发现奶奶的左半边身体,完全失去知觉、没有反应,诊断为中风。开了不少治疗中风的药物。从此,奶奶半身不遂,动弹不得,不能言语,一切生活得靠人服侍。
服过不少药,但效果不明显。我们也多方打听,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。后来,有人介绍了一种民间的治疗方法,说鬼竹子水能治疗中风。于是,我们赶快到山上去找鬼竹子。那时人穷山光,我们生产队山上能找到的鬼竹子不多。为了给奶奶治病,不得已,我们只好跑到邻近生产队山上寻找。偷偷地从别人山上砍了一捆鬼竹子回来。我们先把鬼竹子的枝叶去掉,将鬼竹子按竹节截成一段段,然后再将一段段的鬼竹子斜放在炭炉上,在鬼竹子的低端置盛接鬼竹子水的盘或碗。炉炭生火加热,在其上的鬼竹子受到烘烤后,就从竹筒里慢慢地滴出水来。我们继续给奶奶服用医生开的药的同时,辅以服用鬼竹子水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,奶奶的病情逐渐好转,从不能言语到可以说话,原先失去知觉的左半身也渐渐地恢复了知觉,后来竟奇迹般地恢复到可以自己下床活动,生活也基本上恢复了自理能力。
毕竟中风后大脑严重受损,奶奶身体并没有完全恢复到中风前的水平。说话语音不清,有时行动怪异,不时做出一些令人诧异的事。例如,有时将柴碎垃圾丢进煮好的粥中,有时将汁缸里的水当水缸里的水倒去煮饭煮菜。
与其他农村妇女一样,奶奶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也是根深蒂固,得病后神志模糊,更是经常无端骂大妹妹。即使这样,大妹妹仍尽心尽力服侍奶奶。奶奶自中风后,大约两年多的时间,病情时好时坏、反反复复。轻时,能说话,可下床,基本上恢复生活自理能力;重时,无法说话,大小便失禁,经常弄脏床褥。这段期间,难为与奶奶同床共寝的大妹妹了。她经常给奶奶擦身、换衣服、洗床褥。那些又脏又臭的工作,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。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,能够那样毫无怨言、尽心尽力地服侍奶奶,没有一片真诚的孝心能办得到吗?
有一次,我劳动回来,在厨房里的奶奶叫我进去。原来奶奶在厨房里静悄悄地焖饭。她将焖好的饭分给了我一半,半碗略带异味、有点灰色的白米饭。看到眼前年迈体衰、白发苍苍、已风烛残年的老奶奶。还因为饥饿,要自己动手煮饭,我心中感到不胜的辛酸,不胜的悲凉。在那“十一锄头下去,才有一锄头是农民自己的”特殊年代。像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,除了“仓鼠”,又有哪家能吃得饱呢?我们哀叹这吃不饱、饿不死的现实,却又无力改变现状。奶奶中风,大脑受损伤,许多事情都忘了,却没忘记对儿孙的爱。那半碗饭让我特别感动。那一刻,我就想如果能赚到钱,我一定要让奶奶吃得饱,吃得好。令人遗憾的是,当我有能力孝敬奶奶时,历尽艰辛、受尽欺侮的奶奶已离开我们,报孝无门了。
奶奶在患病时,曾一再呼喊:“阿南,阿南……”,可是当一九七七年,五叔从郑州回来看她时,她却没能认出五叔。在五叔回返郑州之际,见到了日夜思念的“阿南”后的奶奶,大概已了却心愿,也匆匆登上了回归天国的路程。得知奶奶病情骤然变化后,五叔在开车前十分钟,退了上梅县的车票,从湖寮赶了回来。此时,奶奶已被转移到大厅临时搭起的挂有蚊帐的床铺上。一息尚存的奶奶闭目昏睡。五叔悲伤地哭声,令周围的人都禁不住心酸落泪。可是奶奶已无力睁大眼睛,再看看急急赶回来的“阿南”了。到了第三天凌晨一点多,正当我们因连日担忧、守候,而困盹入睡时,与病魔博斗了两年多的奶奶,在那茫茫的漆黑深夜,悄悄地走了,走了,永远,永远地走了。不管儿孙们怎样的呼天抢地哀哭,奶奶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看看她的儿孙们,奶奶从此走了,走了,永远,永远地走了。
今年清明时节,继八五年大团聚后,我们家族共十八人,回乡祭祖。其中我家四人,五叔家七人,满叔家五人,还有两个从南洋回来的大伯的儿子夫妇。我们开两部面包车,于五月二日早上九点多回到老家。大家稍作休息后,便到横屋厅准备祭祖。事先准备好的祭品摆好后,由爸爸主持祭祀。大家分批在祭台前拜祭了列祖列宗。拜祭完毕,燃放两大串,各一丈多长的鞭炮。“劈劈、啪啪”的炮竹声,震天动地,山鸣谷应,静静的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了。
放完鞭炮,紧接着去上坟。首先到泉头陂屋背岗,上奶奶的坟。泉头陂是我们那形似荷叶的村庄的水口,村子三山环绕,这是前后两座青山相对合处。也是前后两座青山山龙(脊)交汇处,中间有流水潺潺的小溪,两座青山宛若两条青龙同时低头在溪中吸水。有座连接这两条青龙的水泥桥,四十年前由满公出资,爸爸负责兴建。由于年久失修,桥栏和围墙的表面已脱落,斑斑驳驳,使那座桥看上去显得那么的苍老。桥两边爸爸亲手栽种的相思树,已长成枝繁叶茂的森森大树,泥竹麻竹也硕大茂密,摇曳多姿。奶奶的坟墓就位于泉头陂东边屋后的山龙上,前方开阔,对面青山,脚下村舍,尽收眼底。那里,青松绿杉,郁郁成荫,蜂鸣蝶舞,相当幽静。静下来,能听到花草树叶颤动时的飕飕风声,能闻到随风飘来的山花的阵阵幽香。厌倦了喧嚣烦躁的城市生活的人,到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超尘脱俗的宁静。
奶奶的坟墓与众不同,墓碑略偏,祭台下有爸爸撰写的墓志铭。墓志叙述 “罗母萧氏招娘,公元一八九一年癸已八月初七日生于高陂,一九七七年丁已九月廿四日卒,享寿八十五岁。…… 在家奉敬翁姑,教育子女,克勤克俭,任劳任怨。且待人仁慈,乡里称誉。懿德长存,永垂不朽。”
来到奶奶的墓地,大家围绕在坟墓前,由满叔向奶奶祷告。七十多岁的满叔哽咽地喊了声:“阿姆,阿兰来看您了”,便悲伤地泣不成声。泪流满脸的满叔一边断断续续地祷告,一边用湿纸巾将墓碑和墓志铭上的黑色霉苔擦去,好让奶奶更好地看看眼前的子孙。
奶奶魂归天国已好几十年,她的满堂儿孙遍布海内外,个个都学有所成,在各行各业做出了成绩。今天追忆奶奶与我们一同经历的那段凄风苦雨的艰难历史,缅怀奶奶,仍难掩悲伤之情。我们要发扬奶奶留下的勤劳俭朴、仁慈宽厚的优良传统,争取作出更大的成绩。
风飕飕,
香幽幽。
翠竹松杉花草幽,
潺潺溪水流。
人去后,
懿德留。
优良传统永不丢,
子孙争上游。
注:照片是作者三代同堂的照片,中间两位老人是作者的爷爷、奶奶。奶奶抱的婴儿就是作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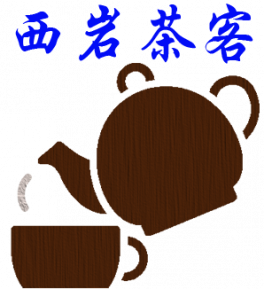
 Users Today : 1
Users Today : 1 Users Yesterday : 2
Users Yesterday : 2 Users Last 7 days : 25
Users Last 7 days : 25 Users Last 30 days : 88
Users Last 30 days : 88 Users This Month : 63
Users This Month : 63 Users This Year : 1016
Users This Year : 1016 Total Users : 9996
Total Users : 9996 Views Today : 1
Views Today : 1 Views Yesterday : 2
Views Yesterday : 2 Views Last 7 days : 28
Views Last 7 days : 28 Views Last 30 days : 113
Views Last 30 days : 113 Views This Month : 74
Views This Month : 74 Views This Year : 1226
Views This Year : 1226 Total views : 24186
Total views : 24186 Who's Online : 0
Who's Online : 0